| 论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01-31 |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形态是金融刑法立法技术的重要环节,它主要解决金融刑法对某种类罪的规范是设置为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目的犯还是非目的犯的问题。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则主要是指金融诈骗罪在立法设计上究竟是以结果犯为模式还是以行为犯为模式。我国《刑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除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之外的其他七种犯罪,都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危害结果。可见,我国金融刑法中,金融诈骗罪客观构成形态主要以结果犯为模式。这种立法安排是否妥当呢?
从立法背景来看,我国金融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主要规定为结果犯是有其历史渊源的。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金融诈骗罪,司法实践中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在单行刑法出台之前或者单行刑法未有涉及的情况下,一般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后来,我国刑事法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独立出来,主要是“考虑到这几种诈骗都发生在金融领域,犯罪分子都利用了金融业务中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远比普通诈骗严重,”同时,“由于普通诈骗罪规定死刑的立法动议多次受阻,故单独规定比较容易对金融诈骗罪增设死刑。”[1]基于此,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普通诈骗罪是一种传统类型的财产犯罪,其以对公私财产权这一法益造成实质性的侵害为既遂标准。各国刑事立法一般都将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于是,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依据结果犯——行为二分理论,结果犯与行为犯在犯罪构成和规范效果上的区别甚大。基本构造上,结果犯是一种完全形态的犯罪构成模式,它以一定的损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的闭合点,强调行为的效果和结局;行为犯则是一种“截短”的犯罪构成模式,它以行为的发生作为犯罪构成的闭合点,强调行为的性质与方式。规范功能上,结果犯注重刑法的谦抑性,倾向于人权保障;行为犯的既遂点则有所前移,它注重扩大刑法打击面,倾向于社会防卫。我国金融刑法将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主要设计为结果犯,意味着:金融违规行为的规制中,刑法介入金融违规行为的环节比较拖后;刑事诉讼中,追诉机关的举证责任较大,犯罪既遂需以欺诈结果之证明为己足;价值定位中,且不论我国金融刑法是否真正做到权利保障,至少其对金融秩序的保障机能是不健全的。基于此,学者们对我国金融刑法的这种立法安排提出较为激烈的批评。如有的学者从金融刑法保护法益性质的角度出发,认为:“金融犯罪主要侵犯的是金融秩序,金融秩序的核心是公共信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规范;为了维护这一社会伦理规范,我们认为,金融法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首选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2]还有的学者从刑事司法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看,以诈骗罪起诉金融欺诈往往事倍功半,如日本发生过的欺瞒交易诈骗案中,对于欺瞒交易中采用的交易形态本身,因为属于合法的交易方式,反对这种交易本身,并不能从正面判为诈骗罪。”[3]当前,有相当多的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德国刑法的立法模式,将金融诈骗罪作为抽象危险犯或行为犯来对待。
二、两种方案的分析
(一)方案之一:行为犯模式
《德国刑法典》第22章中,金融诈骗罪客观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主要采取了行为犯模式。行为犯论者认为,我国金融诈骗罪立法应当借鉴这种模式,综合而言,其依据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金融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系角度,金融诈骗罪属于经济法罪而普通诈骗罪属于财产犯罪,两者保护的法益有着质的区别。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权,而经济犯罪主要侵犯的是超个人法益,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交易秩序。[4]这种质疑,从根本上动摇了通说的理论前提。
第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金融犯罪客观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当有利于刑法对金融犯罪的有效抗制。金融市场中,金融犯罪的防范是一种综合机制,非刑事预防机制与刑事预防机制应当紧密衔接。将金融犯罪规定为结果犯,刑法对金融犯罪的介入将过于拖后,会导致这两种机制的脱节。同时,当损害后果发生之后刑法才匆忙介入,会倾向伴生事后惩治措施所固有的重罪和重刑结构,与我国当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符。[5]因此,为了实现金融刑事法网“严而不厉”的效果,应当考虑将金融犯罪既遂点往前推移,将金融犯罪的客观构成形态设计为行为犯模式。
第三,从刑事司法效率的角度,金融犯罪客观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当有利于对金融犯罪的追诉。一方面,刑事司法效率取决于刑事网络的质量,在刑事网络集中、密集的领域,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监控的可能性比较大,刑事侦查能力较强,刑事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比较容易,这种情况下,“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的运用才具有可能性。金融犯罪行为主要围绕金融市场发生,金融市场是一个法定的、有限的、特定化的人类活动空间,具备使用“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的条件。另一方面,刑事司法效率也受犯罪行为自然犯形状的影响,立法对自然犯主客观方面的技术处理不如对法定犯的回旋余地大。对于作为法定犯的金融犯罪,可以在立法上采用“堵截的构成要件”技术进行规制,[6]以提高刑事司法的效率。
行为犯论者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当然,“敌忾”未必“同仇”,这些不同看法并非完全来自结果犯论者的反驳,更多的则是基于学者对行为论者观点的进一步反思。对行为犯论者的质疑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7]抽象的危险犯概念自被提出时起,就遭到批评。且先撇开危险概念的“行为人危险性说”不论,单就“行为危险性”的含义,德、日刑法理论上就存在较大争议。比如,何谓“抽象危险”?刑法对抽象危险进行处罚的依据何在?[8]并且,危险犯将犯罪既遂点提前,注重社会防卫,使用不当有侵犯人权的危险。
第二,金融诈骗罪中引入“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会造成金融法法益保护的“马太效应”,有悖于刑法谦抑性,不利于人权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及金融刑法原本就存在严重的“金融机构中心主义”倾向,在主体设置上,金融诈骗罪主要是针对“客户”进行的。“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的使用,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降低追诉机关的举证难度、扩大金融刑法的打击面,这对“客户”的利益保护无疑是雪上加霜。
第三,抽象的危险犯真的是《德国刑法典》中金融诈骗罪的唯一表现形态吗?有学者经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比对后认为,德国刑法金融欺诈的行为模式共有三种: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与行为犯,而不是像我国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有抽象危险犯一种模式。[9]比如《德国刑法典》第265b条规定的信贷诈骗属于抽象危险犯,而第266b条规定的滥用支票和信用卡属于具体危险犯,第148条伪造有价票证、第151条有价证券以及第152a条伪造支付证卡和欧洲支票的票样等犯罪则属于行为犯的模式。我国学者或者认为德国刑法金融诈骗罪只有抽象危险犯一种模式,或者将行为犯和抽象的危险犯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10]是对德国刑法理论的一种讹误。
(二)方案之二:预备犯的启用
破而后立,在质疑行为犯论者观点的基础上,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种理论值得我们关注,即“在目前情形下,对于我国金融诈骗罪采用的结果犯的立法模式的弊端,不能总奢望通过立法修改采纳本身也存在缺陷的行为犯模式来解决,而应充分利用我国刑法典的特色规定:在总则中规定对犯罪预备的原则性处罚,这不同于德日刑法典中只在分则中例外地处罚预备犯的立法例,我国犯罪预备的独有特色的立法例,完全可以弥补我国分则中无抽象危险的构成要件的缺憾,事实上使刑法防线比抽象危险的构成要件中更为前移,使法益的保护更为早期化。可惜的是,我国刑法典这一特色立法例,未引起学者和司法部门的应有重视,将宝贵法条资源浪费却倡导拿来主义。”[11](我们可以将持这种主张的论者称为预备犯论者。)预备犯论者和行为犯论者一样,对通说持批判态度,但却另辟蹊径地提出一种不同的方案。这一方案看似更加务实,但是否更加可行呢?
预备犯论者也意识到,我国《刑法》中的预备犯“未引起学者和司法部门的应有重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将希望寄于一个人们都不重视的、近乎“休眠”的规定呢?而实际情况是,预备犯并非像学者所言的那样未引起重视,我国关于预备犯理论研究的文献也是难以胜数,只是预备犯实在是一个比危险犯更加“危险”的概念。诚如预备犯论者所言,预备犯“事实上使刑法防线比抽象危险的构成要件中更为前移,使法益的保护更为早期化”。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很少处罚预备犯。我国《刑法》规定处罚预备犯是受前苏联的影响。但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由于预备行为对于法益的危害是间接的,只有其危害具有相当危险性的时候,才可例外地予以处罚。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以及司法证明的难度,实践中很少见到触犯预备犯的情形。立法上的全面规定,主要是出于严密刑事法网、震慑犯罪的考虑。[12]所以,对预备犯的处罚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刑法功能剑走偏锋、侵犯人权。这就是预备犯为何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处于近乎“休眠”的原因,而不是说人们不重视它。金融刑法应当具有经济性,刑罚过于苛厉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萎缩,影响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尽管在实现入罪功能上,预备犯比抽象危险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过犹不及,不宜采用。
三、一种新的理论分析
对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需要明确争论根本的对立点所在,才能找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金融诈骗罪客观构成形态的争论,对立的根本点就在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性质理解的分歧:如果认为金融诈骗罪主要侵犯了金融秩序,金融刑法应当定位于社会防卫,采取行为无价值立场,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行为犯;但是如果认为金融诈骗罪主要侵犯了公私财产权,金融刑法就应当定位于权利保障,采取结果无价值立场,那么,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也就无可厚非了。
虽然我国金融刑法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但从立法进程来看,其并非是基于对法益性质的定位,出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初衷,只是一种立法惯性使然。然而,我国金融刑法却存在较为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一直将“超个人法益”看作是首要保护的对象。这样一来,就出来了一种现实与价值的悖反、模式与目标的错位。这种情况下,改造我国金融刑法就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金融诈骗罪法益是金融秩序的传统立场,将本类罪改造成行为犯模式;再一个就是转变法益保护的基本立场,将公私财产权作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维持本类罪为结果犯的传统立法模式。行为犯论者无疑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而预备犯论者也认为:“从长远看,在修定(似为笔误,应为‘修订’——引者注)刑法时,也可考虑将部分金融诈骗罪采用行为犯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提醒司法人员注意。”[13]可见,尽管具体方案有所不同,但在法益性质的基本立场上,行为犯论者、预备犯论者和通说都是一致的,都将立论的基础建立在“金融犯罪的主要法益是金融秩序”这个命题之上。然而,我们认为,这种立论值得商榷,后一种模式才是我们的应然选择。
首先,上述几种观点是对德国刑法理论的误读。[14]国内文献在谈及德国经济犯罪时,多认为经济犯罪主要侵犯的是超个人法益,并以此为据来论证我国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这种观点,实为对德国刑法理论的误读。误读之一,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确存在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的划分,但是在二者的关系上,德国通说一般认为超个人法益并非超越、优位于个人法益之上的法益。相反,超个人法益仅仅是个人法益的集合,是对不特定的个人法益的抽象表述。二者之间没有质的界限,只有量的区别,超个人法益归根到底仍然是个人法益。[15]误读之二,就金融诈骗罪而言,德国刑法中与我国《刑法》规定具有可比性的犯罪有两类。第一类犯罪包括第264a条投资诈骗、第265条保险的滥用、第265b条信贷诈骗以及第266b条滥用支票和信用卡,它们同属于第22章诈骗和背信。与我国金融诈骗罪“主要”与“次要”客体之分不同的是,这几条规范在所保护的法益问题上是“直接”与“间接”之分,即认为规范所保护的首先是个体的财产,虽然同时也保护有关的金融交易的安全与秩序,但这种保护仅仅是一种间接性的保护。这种间接性保护的意义主要在于对法律基本原则的确信,规范保护的核心仍然是财产权。第二类犯罪包括属于第八章货币和票证的伪造,包括第148条伪造票证等。这类犯罪保护的是金融票证和有价证券的安全性和功能,而不是财产。由此可见,涉及金融欺诈的德国刑法规范,虽然认可超个人法益的存在,但并非将其作为超越个体法益之上的主要法益进行保护。[16]
另外,金融诈骗罪确系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金融诈骗罪理应是诈骗罪之一种。既然诈骗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金融诈骗罪也应如此,不应因为前者前面有了“金融”二字,就白马非马了。在日本,金融诈骗罪主要由其刑法典第三十七章诈骗罪和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的相关伪造罪来规制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日本就不注重对金融秩序的保护。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罪侵害的根本法益是公私财产权,金融秩序是其间接法益。我国金融刑法对金融诈骗行为的规制应当转变基本立场,以权利保障为首要目标,维持当前立法中的结果犯模式。只是在构成形态及罪状安排等立法技术上需要再进一步完善,让金融刑法权利保障的基本立场贯彻地更加彻底。
上一篇文章: 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下一篇文章: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认定与适用
|
|
|
|
|
| 何焕明 律师 |
| [律师简介] [业务范围] |
| 手 机1: |
13928773272 |
| 电 话: |
020-38399366 |
| E-mail: |
1435630199@qq.com |
| Q Q: |
1435630199 |
| 地 址: |
广州天河体育西路103号维多利广场A座1404室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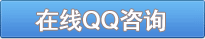 |
|
 关闭
关闭